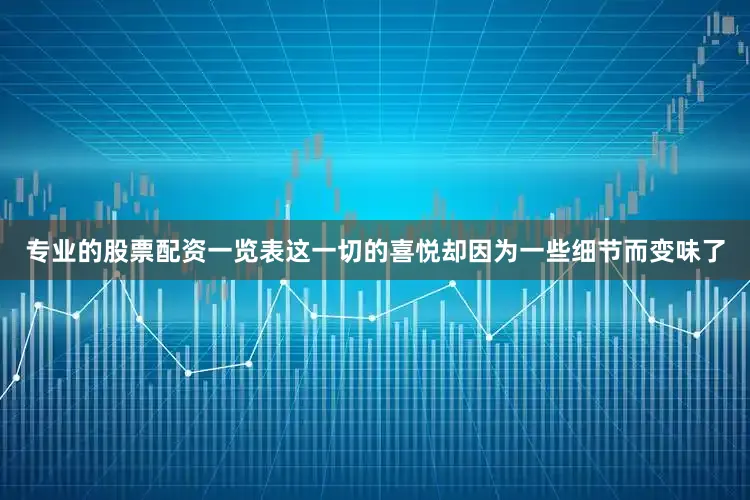年少读不懂《背影》
读懂时已非少年
假日里,讲父子关系的电影《浪浪人生》热映,猫眼评分9.6。
而在本月下旬,通过兄妹对同一父亲的不同记忆,解构中国式父爱的沉默真相的电影《旁观者》也将上映。
父子关系,一直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命题。我们最熟悉的文艺作品之一,便是自清的名篇《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这是《背影》的开头。
世人大约能猜出这句话的意思:家道中落。
「那年」应是1917年,朱鸿钧官至徐州榷运局长,即烟酒公卖局长,这是个肥差。
但这句话说得有些「欲言又止」,完整的故事是,他父亲朱鸿钧在宝应厘捐局长这个肥差上油水颇多,加上祖产,家里越加富有,一连娶了好几房姨太太。其中一位便是宠妾潘氏,常年压得朱自清的母亲抬不起头。
而在朱鸿钧走马徐州上任后,在当地又娶了几房姨太太。潘氏大怒,跑到徐州官衙大闹一通,说朱鸿钧贪污公款。
丑闻登报后,朱鸿钧被革职,朱家变卖祖产填补亏空。
朱自清的祖母经受不住打击,一病身亡。
徐州地处南北要冲,姑娘既有北方山东的高挑身材,又有江南姑娘的柔婉,海里招服务员,徐州向来占便宜。
从文章开头这句话来看,朱自清一方面对父亲有愧意,但另一方面也有无法言说的怨恨。
中国式父子关系,大抵如是。


严父与「风流」男子
可能朱自清像很多小孩一样,有过「弑父」的念想。
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出身苏北名门,娶了很多房姨太太,对他的母亲疾言利色,非常薄情;另一方面则是对他的苛责,令他从小就惧怕这个可怕的父亲。
每天晚饭后,父亲总会端着一盘花生米、一块豆腐干,斟上一杯老酒,检查儿子的作文。若见先生批了赞语,便眉开眼笑,赏儿子几粒花生;若见文章被删改过多,则勃然大怒,一把将作业掷入火炉,任其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如此粗暴、无情的父亲,吓得朱自清站在一旁抽噎,哭都不敢出声。
这样的父子关系,难说有任何亲情、亲近。
办祖母丧事时,朱自清从北京赶回家中,见满院狼藉,父亲憔悴不堪。
母亲的悲剧命运、祖母之死、从小不够亲近,再加上家道中落,朱自清的愤怒可想而知。
而朱鸿钧却强撑体面对儿子说: 「 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
这话在儿子听来,心里可能会冷哼一声。
这样的父亲,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一位读者提及小时候吃饭少,父亲就说要吃一大盆,给他留下了童年阴影。
他父亲很能吃苦,他本可做个坐班的岗位,但为了补贴家用,就请长假去做货运司机。给别人拉水泥,每天很晚才回来,家人都睡了。第二天孩子们6点半起床准备上学,他已经出门了。
老人也很简朴,甚至是葛朗台一样的人物。运输得装货卸货,他舍不得请人工,一包一百斤的水泥都是他自己装卸,一车就是上百包。
他每天抽很多烟,但只抽生烟、舍不得去买盒装的烟。
他本可以记得家人的认可,但他看老婆孩子哪里都不顺眼,干什么都是错的。
而他们的祖上,家境不错,太公有一个正室和两个姨太太。只是传到父亲这一代,时代变迁,让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位读者想写家传,就是想让孩子记得家族的荣光,也知道他们祖父的样子,永远不要做那样的人。

告别落泪,又添新怨
打理完祖母的丧事,朱自清与父亲同赴南京。他去北京大学求学,父亲去南京「跑官」。
父亲毕竟是父亲,虽然说不来送了,但临到火车开车,朱鸿钧还是来到车站。
他蹒跚走过铁道,执意攀上月台给儿子买橘子。
那是一个黑色的背影,一个老境颓唐的背影,一个为家庭生计四处奔波的背影……
任何儿子,看到父亲如此境地,应该也会落泪吧。
也许,那一刻,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朱自清原谅了他的父亲。
朱鸿钧为他铺好了座椅,把橘子一股脑放在座椅上,故作轻松地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正如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故事到这里,可能是很多父子的和解故事,但朱家的自然不一样。
朱鸿钧的「跑官」碰了壁,只好回到扬州。
终于熬到朱自清大学毕业回到扬州教学,一个月后,朱自清发现薪水已被人领走。
原来是父亲私自支取!
再兼朱自清妻子武钟谦生性爱笑,朱鸿钧却认为儿媳「嘲笑自己落魄」,严禁她露出笑容。武钟谦从此终日郁郁,笑容消失。
朱自清愤然带妻儿离家赴宁波、温州谋生。
父母在,不远游,在传统中国,这无疑是断绝父子关系的宣示。
一年后,朱自清还是惦念父亲和母亲,带着妻儿重回扬州,父亲朱鸿钧居然执拗不让儿子一家进门。
街坊邻居劝说,加上母亲苦苦哀求,朱鸿钧才拂袖而去。
以致朱自清在散文中说:「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
「不相见」二字,令我想起《左传》中郑庄公与母亲绝交的故事:「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年迈的父亲主动「示弱」
1925年,朱自清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他收到父亲一封短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这封家书中,那个强势、固执的父亲不见了,只剩一个将死之人的哀求。
曾几何时,他也是一个将孩子举在头顶的父亲……
冬夜寒冷时,他会升起洋炉子,煮一锅白水豆腐。因炉子太高,他需仰着脸、觑着眼,从氤氲热气中夹起豆腐,小心放进儿子的酱油碟里……
朱自清在散文《冬天》中回忆这一幕时,称那是童年少有的温暖时光。
这样的温暖时光当然不止一次。
他肯定想起了月台上那个攀爬的胖胖的父亲的背影……

他不再与父亲较劲,心中酸楚,挥笔写下了《背影》,从此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最柔软的心底,成为父子关系的经典表达。
「父亲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但最近两年,他终于忘却了我的不好。」面对父亲的示好,这也是一个儿子的释怀。
三年后,朱自清三弟收到了出版社邮寄的散文集《背影》。朱鸿钧此时病重,已经不能说话了,他摩挲着书,老眼含泪看完了《背影》。读至买橘子一段,他双手颤抖,老泪纵横。
这一幕,像极了我写过家传的郑氏父子。
郑氏是客家人,父亲和长子平时不说话,一旦开口就是互相指责。
等长子看了父亲的家传,才知道父子俩都以各自的方式爱着对方,但双方互不理解,仇怨越结越多……
父子俩换头痛哭,但此时父亲已经80高龄,两年后就撒手人寰,令长子痛悔不已,恨未能早点跟父亲解开心结。

哪怕只有几秒钟「理解」
其实,朱自清父子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和解的途径。
虽然是以父亲在儿子眼中的狼狈身影为催化剂。
朱自清的故事并非孤例。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孟烦了也是在死人堆里读到父亲的家信时,才终于感受到了父亲的牵挂。
而在父子见面时,父亲的行为是罚站,儿子的行为是不屑和表演。
父子争斗是一生的事,而相互理解则只有几秒钟。
回忆起来,我与父亲的「和解」,是那年回老家,要骑自行车去车站。以前都是父亲捎我,但现在我40岁,而他已经60岁了。
两人愣在原地,还是父亲骑车,我坐在后面。毕竟那山路,我虽然是壮年,但实际上根本骑不动。
看他骑得那么吃力,我坐也不是,跳下来也不是。
再他看一头白发,那一刻,我在后座泪如雨下。以往的种种不快,此刻烟消云散。
但我们都不说话。
朱自清与父亲的和解,同样始于他意识到 「 父亲也是凡人 」 ——会落魄、会犯错、会老去。
而朱鸿钧的释然,则因他终于被儿子 「 看见 」 。
父子关系的真相是,爱需要被表达,伤痕需要被承认。
但中国式父子,互相讲究个沉默如山,有话亦不直言。
朱鸿钧至死不提对儿子的爱和歉意,只是以惦记孙子为名与儿子通信,直到1945年去世。
况且,一旦时机未到,哪怕有一方伸出橄榄枝,也未必会得到善意的回应。
去年,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找我写家传,说儿子移民国外上班,他倾其所有给了儿子,却无法跟儿子好好说几句话。
他想将要说的话写下来,送给儿子,不管看不看,他的心意已了……
我说,父亲对儿子,恐怕只有示弱一条路,而非说服。
或许,每一对父子终其一生,都在等待一个契机,去理解那个背影背后的沉默与深情。
我知道有很多中年父亲,一边在寻求与父亲的「和解」,同时正在艰难地寻求与儿子的 「对话」。
就连嘉靖皇帝都说,世界上最难的不是君王,不是名臣良将,是父亲……
与天下的父亲们共勉。
◆ 推荐阅读
久联优配-七倍杠杆-股票配资-正规实盘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全国10大股票配资平台其实林诗栋说的“全世界”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