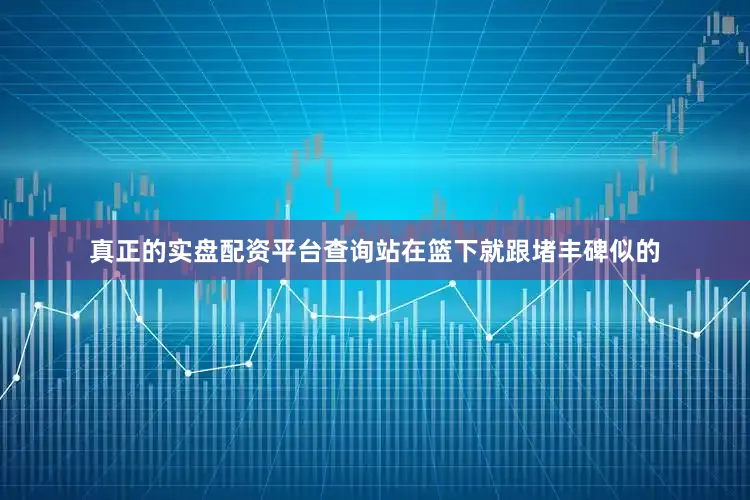【考古纪实:祁连山惊现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2019年盛夏,甘肃省天祝县国土局在岔山村北侧一处风化严重的山岗实施土地整治时,几名工作人员在翻动表层土壤时突然发现了一批形制特殊的青灰色砖块。这些砖块表面布满岁月侵蚀的痕迹,边缘处还残留着精美的莲花纹饰。意识到这可能涉及重要文物,现场负责人立即启动文物保护预案,层层上报至天祝县文物管理局。
县文物局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当天便派出由副研究员带队的三名考古专家赶赴现场。经过为期两周的钻探调查,专家们在地下3米处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砖室墓。墓葬坐北朝南,采用典型的唐代\"刀把\"形制,墓室面积达50平方米,墓道两侧还保留着完整的排水系统。如此高规格的建制让考古队员确信,这位长眠于祁连山麓的墓主人必定是唐代显贵。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这位权贵会选择远离中原的边陲之地作为安息之所?
展开剩余81%(配图:祁连山脉全景,展现墓葬发现地的地理环境)
随着勘探深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抢救性发掘申请。获得批复后,一支由30余名专业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祁连山。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墓室封土时,一组令人震撼的唐代艺术珍品逐渐显露真容:两扇高约2.5米的柏木墓门虽已腐朽变形,但门上排列整齐的50枚鎏金铜泡钉仍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门楣处残存的铜锁构件显示着当年严密的防盗措施。更令人惊叹的是门楣上方保存完好的壁画,画面中巍峨的宫殿建筑与墓门形制如出一辙,朱红色的廊柱与青绿色的斗拱依然色彩鲜明。
(配图:墓门特写,突出鎏金铜泡钉与壁画细节)
进入墓室后,考古队员在东西两侧发现了70组彩绘陶俑。这些陶俑平均高度约40厘米,采用\"模制彩绘\"工艺,人物表情生动传神。西侧43组俑群以文官仪仗为主,东侧27组则是胡人商队形象,其中牵驼俑、乐舞俑的服饰纹样仍清晰可辨。如此规模且保存完好的俑群在西北地区实属罕见,考古领队王教授当即判断:\"这很可能是某位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边疆重臣之墓。\"
(配图:彩绘俑群细节,展示不同人物造型)
当清理工作推进到墓室中央时,堆积如山的随葬品让考古队面临严峻挑战。铜器、漆盒、陶罐等器物相互叠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损坏。考古队紧急搭建起钢结构作业平台,采用高空悬吊方式逐层清理。就在平台搭建期间,一个重大发现让所有人屏息凝神——在墓室正中位置出土了一方完整的青石墓志。这方边长80厘米的墓志采用罕见的双层设计,上层盖石阴刻\"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九个篆书大字,下层志石与盖石之间还垫着多层丝绸衬垫。
(配图:双层墓志出土现场,展示丝绸衬垫层)
经过文献比对,专家确认\"大周\"正是武则天时期的国号。历史文献显示,当时活动在甘肃一带的吐谷浑王族正是慕容氏。这个曾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政权,在隋唐时期历经多次征伐,最终在吐蕃崛起后走向没落。墓志的发现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配图:吐谷浑历史疆域示意图)
为破解墓主身份之谜,考古队决定将墓志整体移送至兰州文物保护中心。在恒温实验室里,文保专家采用显微分离技术,历时两周终于无损揭取了夹层中的丝绸。这些厚约0.5毫米的丝绸上不仅保留着墨书题记,还发现了精美的联珠纹刺绣。与此同时,墓室内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北壁残存的壁画经红外扫描后,显现出完整的\"金乌负日\"、\"玉兔捣药\"等神话场景;棺床上覆盖的织锦经鉴定为唐代宫廷专用的联珠双龙纹绫,其上的大象纹样暗示着与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配图:实验室分离丝绸过程)
当清理至内棺时,更多惊世发现接踵而至:一具长2.3米的柏木棺椁周围散落着鎏金马具、铁质铠甲等军事装备;东南角出土的彩绘陶仓中竟保存着千年前的青稞颗粒;最令人称奇的是棺前漆盘里的一枚核桃,其果壳纹理依然清晰可辨。这些发现无不昭示着墓主人显赫的军事背景与奢华的生活品质。
(配图:出土核桃与粮食标本)
最终,实验室传来决定性发现:下层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慕容智作为吐谷浑末代可汗的传奇一生。这位被武则天册封为\"云麾将军\"的边疆枭雄,其墓葬严格按照吐谷浑王族礼制营建。更关键的是,墓志明确提及此处是\"迁葬于大可汗陵区\",这一记载证实了祁连山麓极可能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吐谷浑王陵区。这个发现不仅填补了吐谷浑考古的空白,更为研究唐与周边民族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
(配图:慕容智墓志铭文拓片)
发布于:天津市久联优配-七倍杠杆-股票配资-正规实盘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